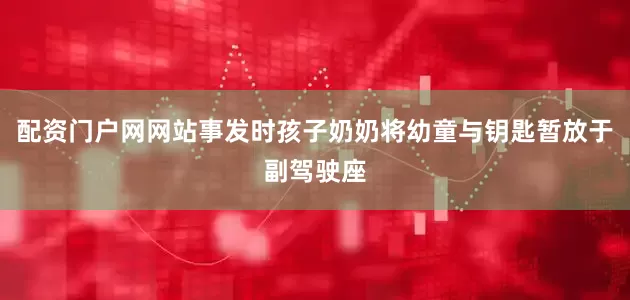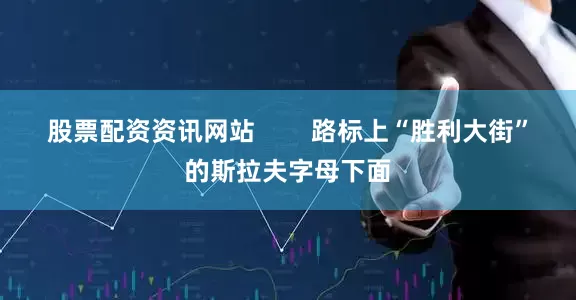
走在南萨哈林斯克的街头,东正教堂的钟声随着风儿飘荡,而胜利广场那纪念碑上的俄文铭文,悄悄掩盖着泥土中半腐的满文界桩。

路标上“胜利大街”的斯拉夫字母下面,隐约还能看出日治时代“丰原市表参道”的凹陷痕迹。
超市里36元一斤的鲜活帝王蟹堆得满满当当,而橱窗海报上的日本动画人物却对着哥萨克风格的木雕笑着——这座岛屿的身份,就像海雾里的废旧灯塔一样,让人捉摸不透。

主权归属的百年博弈
库页岛面积7.64万平方公里,差不多是两个海南岛那么大,但却成了东亚地区一个小型的地缘政治角力点。说到历史,当唐朝在725年设立黑水都督府来管辖库页岛时,中原的治理体系已经走过了千余年的历史。
在1413年,明朝钦差亦失哈在奴儿干城建起了永宁寺,碑上刻着“敕修永宁寺记”,这也成为中央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依据。
在1689年,《尼布楚条约》通过正式的国际条约方式,明确了库页岛属于中国领土,这也是历史上该岛主权最明白的一个节点。

强国间的角逐推动了历史的变迁。
1858年《瑷珲条约》一签,沙俄的兵力就闯上了库页岛,强行登陆。那阵儿,清政府正处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危机之中,不得不被迫签了1860年的《北京条约》。
挺耐人寻味的,这两份条约对于库页岛的归属,都说得挺含糊——只提到“乌苏里江以东之地”,根本没给个明确的范围坐标。
这类法律上的漏洞,也就是争议的根源。有中国学者指出,清政府从未在正式文件里划拨库页岛,而俄方则坚持“实际掌控就是主权”。

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又让这片岛屿变得更乱,1905年签的《朴茨茅斯和约》把北纬50度线以南的地区划给了日本,还叫它“桦太厅”。
1945年苏联全盘接管后,这片土地上的48.9万人口里,90%都成了斯拉夫移民,土著民族只占不到5%。当俄罗斯国旗升起的那一刻,法律和现实之间的差距,再也难以弥合。

身份认同的撕裂与共存
在列宁广场的壁画边,日语招牌的居酒屋彻夜喧嚣着,俄罗斯妈妈帮女儿穿上阿伊努传统服装参加文化节,这些梦幻般的画面,展现了库页岛内部那些复杂的矛盾。
殖民时期留下的痕迹还挺深刻的,比如日本统治时期建的丰原市役所建筑,现在变成了库页岛博物馆,里面展出了日俄陆上界碑,院子里散落着一些苏联坦克的残骸。
更让人觉得怪诞的是,那边滑雪场的宣传册竟然说自己是“俄罗斯前三名的滑雪胜地”,可偏偏用“JAPOW”——那是日本粉雪的代号——来吸引游客。

这种文化交融带出了点特别的氛围,新一代库页岛人把混合身份当成一种新的认同感,就像南萨哈林斯克美术馆的策展人说的:“我们不一定非得选俄国人或者日本人的身份——库页岛人就是我们真正的归属。”
在压力之下,原住民文化依然努力生存,尼夫赫人曾经占据岛上80%的人口,现在只剩下大概4500人。他们的语言和其他语系都不一样,被语言学家誉为“古亚细亚的活化石”。
在政府推动俄语教育的政策之下,乌德盖族中用母语交流的人不到百人,老人们还在坚持传承“虎族传说”,可年轻一辈反而更熟悉莫斯科的流行歌曲。

被掩埋的记忆战场
契诃夫在1890年到库页岛时,在《萨哈林旅行记》中写到清国遗民的情况:“留着辫子的男子指着庙街那边说,‘那曾经是我们的土地’。”
如今契诃夫公园里竖着他的铜像,可雕像底座上的铭文只提到“揭露沙俄的流放制度”,对之前的那些历史背景就一点也没提。

这种对历史故事的选择性删除,真是无处不在,随处可见。
那岛上的教材把1858年说成是“俄日联手开发的起点”,完全没提唐朝到清朝这段治理历史。
游客在美术馆里看到唐代书法,导览词却说它是“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赠礼”,避开了它作为朝贡制度文物的真实身份。
更让人感慨的是,日本探险家1792年在爱努酋长家里找到的乾隆四十年的满文档案,现今存放在北海道大学图书馆——而在国内却没有清代档案的原件。

因为资源和利益的关系,导致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被压制沉默了。
库页岛的石油储量已经确定达到7亿吨,天然气储量则有7000亿立方米,每年的渔获量也超过百万吨。
中俄企业联合开发的“萨哈林-2号”油气项目,总投资达200亿美元。钻机发出轰鸣声时,泥土深处的永宁寺碑碎片也没人再去理会了。

被工具化的过去与拒绝反思的现在
库页岛对历史的划分,可以说是典型的切割式处理。
胜利广场上的那把“永恒火焰”燃烧着,纪念着1945年苏联击败日本的胜利,然而,却把1904年俄军拆毁明朝永宁寺、掠夺碑刻到海参崴的那些旧账给忘了。
那边的博物馆摆出气势汹汹的日俄陆上界碑,可说是不遗余力,但对于1689年《尼布楚条约》里面写的“库页岛归大清”的那段内容,却一句提都没有。

有时候,人们会选择性地忘掉一些事情,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眼前的利益。
一旦俄罗斯把库页岛打造成为“远东能源宝库”,在那里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的产量占了远东地区的23%,那么任何关于历史的追溯都变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。
在岛上的鱼市上,活帝王蟹每斤只卖36元人民币,场面热闹非凡,可没人关心为何中国渔船得向俄方付高额的捕捞费。
更搞笑的是,当俄罗斯年轻人在滑雪场玩“俄式荒野探险”的时候,他们脚下那片土地曾是鄂温克猎人的神山呢——开发主义正把殖民者当年的未完成的文化清洗给搞定了。

无主之地的身份困境
在库页岛机场的免税店里,尼夫赫人的鹿骨雕塑和套娃摆放在一起,包装盒上写着“正宗俄罗斯手工艺”。
那家由韩国移民开的餐馆里,端出了所谓的“萨哈林特色蟹肉寿司”,声称是融合了三国的精华菜肴。
这些商业符号就像是岛屿命运的象征——在国际市场上,历史被打扮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吸引点。
学者们为《尼布楚条约》的法律效力争论不休的时候,岛北的鄂罗克老人依旧在祭祀熊灵的仪式里低声吟唱:“海浪把大地分开的时候,我们就已经来了。”
可能啊,库页岛的真正秘密就在这里,所有那些强势势力都只是过客罢了,只有海浪的声音才会一直回荡在悬崖底下锈迹斑斑的界碑上。而每一朵浪花,都是在不停地洗刷人们对土地的执迷不悟。
配资公司官网首页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浙江股票配资平台《1840》由国家电影局指导创作
- 下一篇:没有了